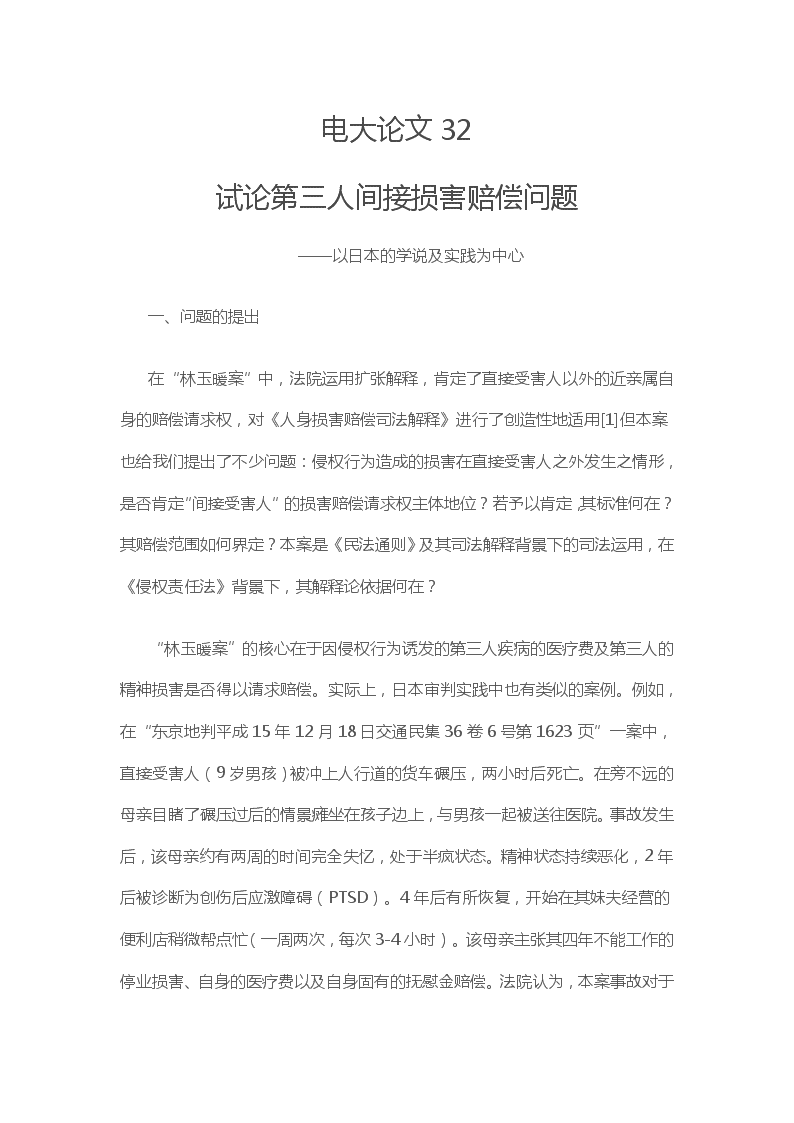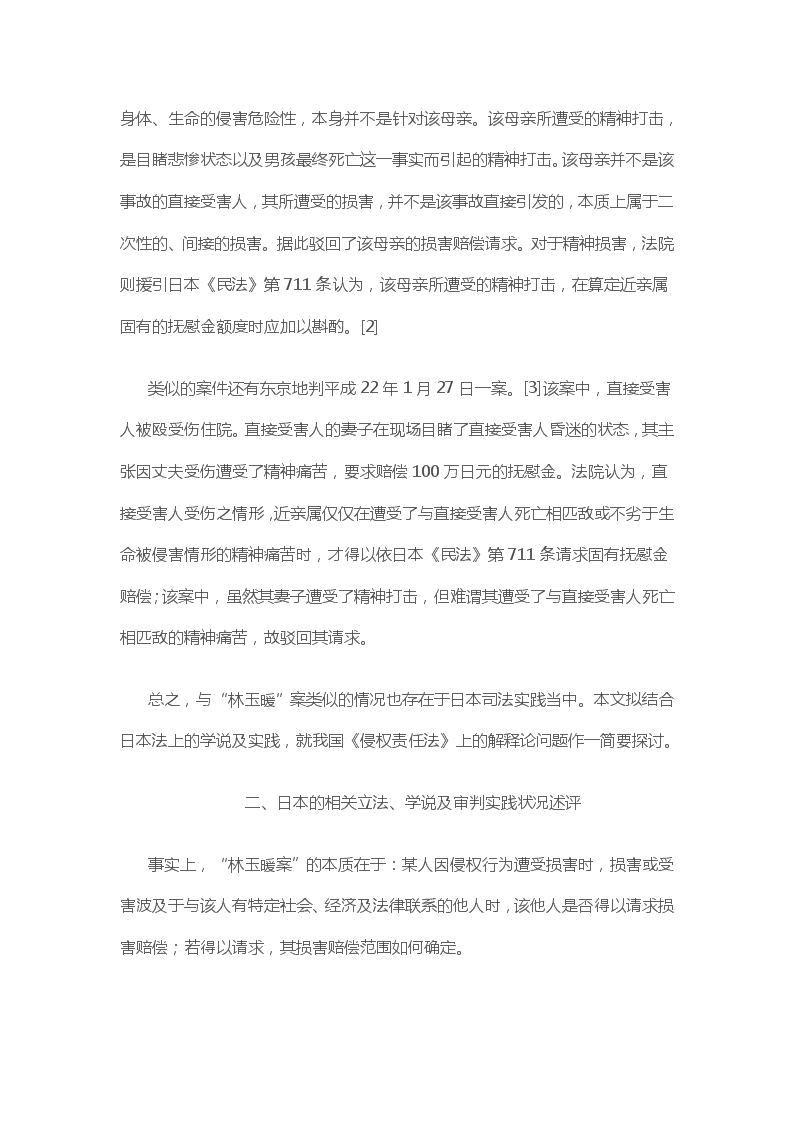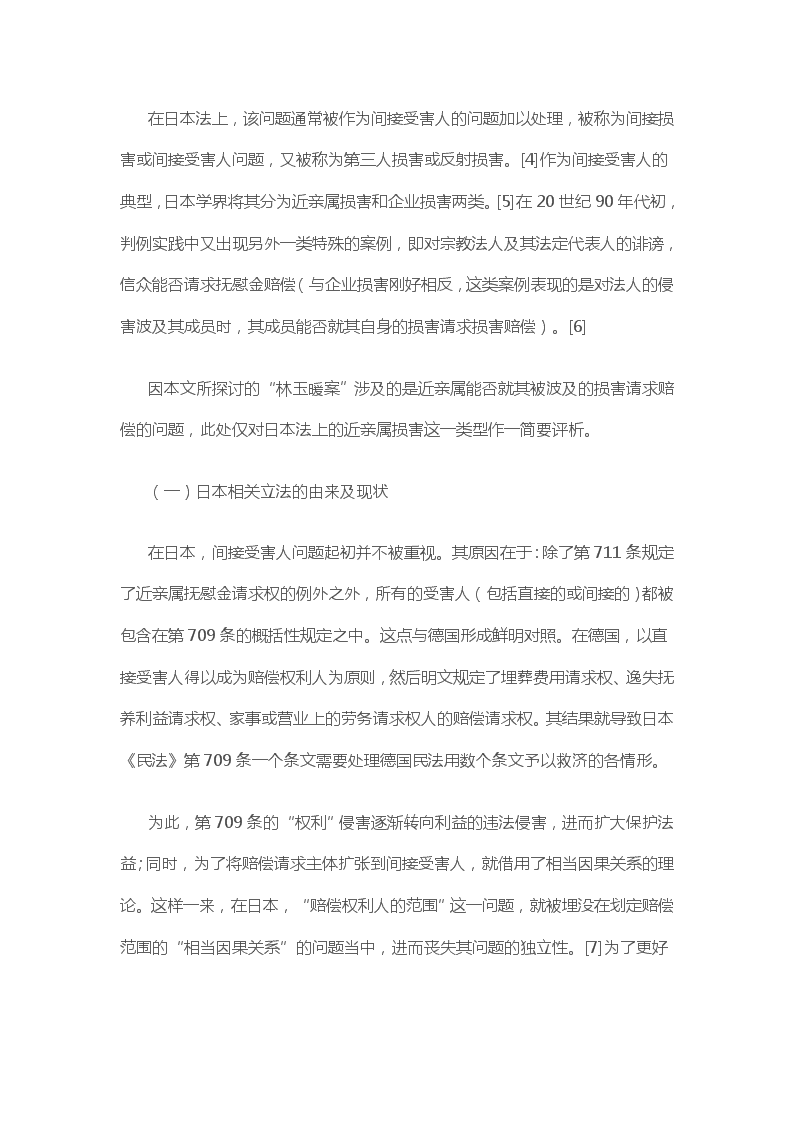- 32.34 KB
- 2022-03-31 发布
- 1、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淘文库整理发布,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请立即联系网站客服。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阅读内容确认后进行付费下载。
- 网站客服QQ:403074932
电大论文32试论第三人间接损害赔偿问题——以日本的学说及实践为中心一、问题的提出在“林玉暖案”中,法院运用扩张解释,肯定了直接受害人以外的近亲属自身的赔偿请求权,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行了创造性地适用[1]但本案也给我们提出了不少问题: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在直接受害人之外发生之情形,是否肯定“间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地位?若予以肯定,其标准何在?其赔偿范围如何界定?本案是《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背景下的司法运用,在《侵权责任法》背景下,其解释论依据何在?
“林玉暖案”的核心在于因侵权行为诱发的第三人疾病的医疗费及第三人的精神损害是否得以请求赔偿。实际上,日本审判实践中也有类似的案例。例如,在“东京地判平成15年12月18日交通民集36卷6号第1623页”一案中,直接受害人(9岁男孩)被冲上人行道的货车碾压,两小时后死亡。在旁不远的母亲目睹了碾压过后的情景瘫坐在孩子边上,与男孩一起被送往医院。事故发生后,该母亲约有两周的时间完全失忆,处于半疯状态。精神状态持续恶化,2年后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4年后有所恢复,开始在其妹夫经营的便利店稍微帮点忙(一周两次,每次3-4小时)。该母亲主张其四年不能工作的停业损害、自身的医疗费以及自身固有的抚慰金赔偿。法院认为,本案事故对于身体、生命的侵害危险性,本身并不是针对该母亲。该母亲所遭受的精神打击,是目睹悲惨状态以及男孩最终死亡这一事实而引起的精神打击。该母亲并不是该事故的直接受害人,其所遭受的损害,并不是该事故直接引发的,本质上属于二次性的、间接的损害。据此驳回了该母亲的损害赔偿请求。对于精神损害,法院则援引日本《民法》第711条认为,该母亲所遭受的精神打击,在算定近亲属固有的抚慰金额度时应加以斟酌。[2]类似的案件还有东京地判平成22年1月27日一案。[3]该案中,直接受害人被殴受伤住院。直接受害人的妻子在现场目睹了直接受害人昏迷的状态,其主张因丈夫受伤遭受了精神痛苦,要求赔偿100万日元的抚慰金。法院认为,直接受害人受伤之情形,近亲属仅仅在遭受了与直接受害人死亡相匹敌或不劣于生命被侵害情形的精神痛苦时,才得以依日本《民法》第711条请求固有抚慰金赔偿;该案中,虽然其妻子遭受了精神打击,但难谓其遭受了与直接受害人死亡相匹敌的精神痛苦,故驳回其请求。总之,与“林玉暖”案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日本司法实践当中。本文拟结合日本法上的学说及实践,就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解释论问题作一简要探讨。刑法学近3年二、日本的相关立法、学说及审判实践状况述评事实上,“林玉暖案”的本质在于:某人因侵权行为遭受损害时,损害或受害波及于与该人有特定社会、经济及法律联系的他人时,该他人是否得以请求损害赔偿;若得以请求,其损害赔偿范围如何确定。
在日本法上,该问题通常被作为间接受害人的问题加以处理,被称为间接损害或间接受害人问题,又被称为第三人损害或反射损害。[4]作为间接受害人的典型,日本学界将其分为近亲属损害和企业损害两类。[5]在20世纪90年代初,判例实践中又出现另外一类特殊的案例,即对宗教法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诽谤,信众能否请求抚慰金赔偿(与企业损害刚好相反,这类案例表现的是对法人的侵害波及其成员时,其成员能否就其自身的损害请求损害赔偿)。[6]因本文所探讨的“林玉暖案”涉及的是近亲属能否就其被波及的损害请求赔偿的问题,此处仅对日本法上的近亲属损害这一类型作一简要评析。(一)日本相关立法的由来及现状在日本,间接受害人问题起初并不被重视。其原因在于:除了第711条规定了近亲属抚慰金请求权的例外之外,所有的受害人(包括直接的或间接的)都被包含在第709条的概括性规定之中。这点与德国形成鲜明对照。在德国,以直接受害人得以成为赔偿权利人为原则,然后明文规定了埋葬费用请求权、逸失抚养利益请求权、家事或营业上的劳务请求权人的赔偿请求权。其结果就导致日本《民法》第709条一个条文需要处理德国民法用数个条文予以救济的各情形。
为此,第709条的“权利”侵害逐渐转向利益的违法侵害,进而扩大保护法益;同时,为了将赔偿请求主体扩张到间接受害人,就借用了相当因果关系的理论。这样一来,在日本,“赔偿权利人的范围”这一问题,就被埋没在划定赔偿范围的“相当因果关系”的问题当中,进而丧失其问题的独立性。[7]为了更好地了解日本的这一状况,有必要考察日本《民法》第709条、第711条等条文的立法由来。日本《民法》第709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人,对于因此所发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8]同时,其第711条规定:“侵害了他人生命的人,对于受害人的父母、配偶及子女,即使其财产权没有受到侵害也必须做出损害赔偿。”该条直接肯定了特定范围内的近亲属在受害人死亡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日本学说和实践中将其作为遗属固有抚慰金请求权的规范依据。其实,在法典调查会的草案中,并没有与日本《民法》第711条相当的规定,该条是在审议过程中加入的条文。在第709条的草案说明中,认为第709条的“权利”侵害也包含了非财产损害(精神、肉体等的痛苦),接着在第710条正面肯定了损害中包含了财产以外的损害。其理由在于,日本旧民法中曾规定生命权的侵害并不产生侵权之债,为避免生命、身体、自由等的侵害不产生财产损害而不予赔偿的误解,需要对非财产损害的赔偿作出特别规定;同时也是为了明确第709条规定的权利侵害的范围。[9]不仅如此,由于在生命权受侵害情形的抚慰金请求权问题上,立法当初持死者本人并不享有的主旨,因此在第710条的保护法益中删去了“生命”。[10]作为其替代方案,在第711条赋予特定范围内的近亲属固有的抚慰金请求权。[11]
但在日本《民法》第709条的审议过程中,围绕该条规定的“权利侵害”进行了具体审议。横田国臣委员提出,父母被杀害之情形,父母自身受到了权利侵害这点无疑,但是否能说其子女本身也受到了权利的侵害?穗积陈重起草委员对此做了说明:于此情形,若存在抚养权的侵害,则其子女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12]但有人认为,因并非对子女的权利侵害,父母被杀害所引起的痛苦将不予赔偿,而在自由、名誉毁损等被侵害的情形,却得以赔偿;两者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均衡。因此建议删去“权利侵害”要件。穗积陈重起草委员为此作了说明,认为对他人的生命并不拥有权利,因此,于此情形并非权利侵害,若自己未丧失扶养则构不成对自己的权利侵害,由法官自由裁量斟酌其痛苦决定其赔偿额即可。但未得到认可。作为妥协的方案,于是就设置了第711条。[13]结合上述立法过程,关于第711条的立法主旨,日本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学说。[14]一是创设规定说。依该学说,生命受侵害情形的近亲属抚慰金,并不需要独立构成侵权行为,不要求权利侵害要件及过错要件。该学说与死者抚慰金的非继承说具有亲和性。就第711条与间接受害人学说之间的关系而言,该学说通常将第711条视为例外规定,并据此认为应限定其适用范围等,不能任意扩张。
二是确认或推定规定说。随着理论和判例的发展,“法律上保护的利益”也受到侵权法的保护。据此,近亲属的精神痛苦也可以作为“法律上保护的利益”按照第709条和第710条得到保护。按照该理解,第711条只不过缓和了举证责任负担,在生命受侵害的情形,配偶、父母及子女无须举证其构成“固有”抚慰金请求的精神痛苦。在间接损害问题上,持该学说的学者中有认为应当将第711条视为例外而加以限制性地适用;也有认为,第711条只是将侵权行为引起第三人定型损害的情形之一加以明文规定;另外,还有从相当因果关系角度阐述间接损害问题,认为第711条是规定了得以肯定相当因果关系的标准类型之一。任何一种理解都不否定超出第711条范围的来自间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将第711条视为例外规定的解释,对此多持消极态度,而其他几种理解也多主张应当注重相当因果关系中的“相当性”判断。三是限制性规定说。该学说认为,随着权利侵害向利益的违法侵害的变化,作为违法行为的结果,遗属遭受了损害,得以依第709条和第710条请求其损害赔偿,但因生命受侵害时遭受损害的人的范围相当之广,第711条在法政策上限定了得以请求的主体范围。在间接受害人问题上,该学说也持消极态度。从上述规定和学说可以看出,作为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日本《民法》第709条并未限定请求权主体,而是从赔偿义务主体角度作出规定。同时,在第710条明确肯定了生命受侵害情形的特定范围近亲属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虽然在其解释上学界存有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日本民法在立法当初就明文规定了特定范围(配偶、父母、子女)内的间接受害人就特定情形(被侵权人生命受侵害)所享有的特定损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近亲属固有抚慰金赔偿请求权)。与围绕第711条展开讨论的进路不同,日本民法典制定以后也有一些学说围绕第709条对间接受害人的问题作出探讨。因此,也有必要稍微介绍一下第709条涉及间接损害时的立法考量。关于加害人过失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因该他人(受害人)的死亡、受伤致使第三人受有损害时,第三人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向加害人请求损害赔偿,当然要求损害的发生及因果关系的存在,问题就在于过错与权利侵害。
如前所述,民法起草者对于间接受害人也要求权利侵害要件。但与此同时,对直接受害人享有终身年金债权的间接受害人,则以权利受到侵害为由肯定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只不过是因为教授的友谊而受有事实上的经济援助的书生,则以权利未受到侵害为由否定其损害赔偿请求权。[15]由于源于受害人死亡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的范围各式各样,法典调查会也讨论了应当如何限制加害人的责任。起草者拒绝了以预见可能性加以限制的提案,认为“应以权利之有无定其界限”。[16]对于是否要求过错,民法起草者并未言及。山口成树教授认为,如同上述终身年金债权的侵害,加害人得以预见的情形非常少见,若要求过错,也只不过是拟制的过错而已,若是如此,起草者本来应当言及如此拟制的必要性。但之所以在法典调查会上未言及过错,山口成树教授认为可能是起草者及调查会的出席者认为,就间接受害人的权利侵害要求加害人的过错(预见可能性)本身并没有意义。[17]事实上,随着“权利侵害”要件遭到放弃,日本《民法》第709条中的“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否得以涵盖间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正如上述“确认或推定规定说”和“限制规定说”所表明的那样,第709条本身就已经涵盖了解决间接损害问题的可能性。(二)日本的相关学说状况
与起草过程的讨论和制定后不久的判例不同,日本学说后来受到了《德国民法典》的影响,认为只有因加害人的过错行为直接受有权益侵害的受害人才得以成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对于加害人的过错未及于的间接受害人,即使其权益受有侵害,也不能请求损害赔偿。[18]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间接受害人的问题逐渐被提起,并日益发现日本民法的规定并不能完全应对这一领域,于是不得不掺入了法政策判断,也因此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19]日本相关的学说多将其作为损害赔偿范围上的问题加以讨论,基本上主张依相当因果关系来判断。但随着学说和判例的发展,也出现了以下几种主要的学说。仓田法官在“交通事故与企业损害”一文中对公司在因其工作人员的人身事故而遭受损害时也适用相当因果关系来判断加以批判;认为权利侵害向违法性理论的转换,其目的并非在于扩大请求权人的范围,也不在于扩大损害的范围,若对间接受害人也作出救济,就有些过头了。除了仅有的少数例外之外(第711条明确规定的抚慰金请求以及亲属的丧葬费请求),不应将其扩大到一般的间接受害人。[20]
好美教授则认为,援用“相当因果关系”来划定请求权主体,不仅明显背离了该制度的本来目的,而且其判断标准也相当模糊。为避免此等问题,有必要对请求权主体做出独立分析。好美教授认为应当协调受害人一方的保护与加害人一方的预测可能性。对于直接伤亡人以外的第三人遭受的财产损害,好美教授将其类型化为:一是直接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反射到第三人处,实际上与直接受害人遭受的损害相重合的损害,若直接受害人自己提出请求亦被肯定的损害,被称为“不真正的第三人损害”;二是与直接受害人的损害不相重合的第三人固有的真正损害。例如,因工作人员无法工作导致的销售额减少等营业上的逸失利益等。间接受害人为近亲属的情形,好美教授也将其分成转化损害和固有损害加以考察。对于转化损害,因死者不具备权利能力,死者自身无法请求其逸失利益及抚慰金,但本质上这些都属于死者自身的损害或其变形物。若直接受害人只是受伤,则此等损害赔偿请求权原则上属于受害人本人,若近亲属加以请求时,则将其作为因代付而引起的反射损害处理即可。[21]总之,无论是仓田法官还是好美教授,都将间接损害或间接受害人问题定位为赔偿请求权主体问题(亦即是否就间接受害人也成立侵权的问题),[22]认为原则上只有遭受权利侵害的直接受害人得以构成请求权主体,对于加害人的过错行为未及于的间接受害人,即使受有损失,也不能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持类似见解的还有前田达明教授、四宫和夫教授。其主要理由在于:(1)随着日本民法的德国化,将日本《民法》第709条的“母法”来源定位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而《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否定了间接受害人的请求权;(2)将“请求权人的范围”委之于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会导致加害人责任的过大化。[23]也有学者专门讨论了受害人受伤情形的间接损害问题,认为某人受有伤害时,作为该侵权行为的间接效果或反射效果,受害人近亲属也可能遭受有形或无形的损害,但近亲属是否也因此独立取得对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会成为问题。
首先是财产损害。如近亲属由受害人扶养时,因受害人劳动能力的下降、丧失而导致近亲属的财产损害。但与死亡的情形不同,受伤的情形并不存在否定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余地,因此,似乎没有理由肯定近亲属独自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害人受伤情形、近亲属的财产损害赔偿请求中成为问题的是因该伤害而支出的医疗费等近亲属的直接损害赔偿问题。对于近亲属或直接受害人的任何一者都可以请求赔偿这一结论本身,学说本身并没有争议,但在理由构成上大致有四种:(1)家庭集体说(家团说);(2)不真正连带债权说,近亲属的请求权和直接受害人本人的请求权构成同一目的的分别债权;(3)赔偿人代位说;(4)无因管理说。德本教授进一步指出,现在的通说是不真正连带债权说。[24]其次是精神损害问题。虽然有力说认为既然受伤的受害人本人可以请求抚慰金,并没有必要肯定近亲属固有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通说支持判例的立场。德本教授认为,也存在仅仅赔偿受害人本人的财产、精神损害难以抚慰近亲属精神痛苦的情形。但究竟限于何种范围内的近亲属以及何种程度的损害,仍然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25]最近,也不乏强烈主张间接受害人应得到赔偿的理论,其中山口成树教授的主张最为引人注目,并曾在日本私法年会上为此做了专题报告。山口教授认为,在间接受害人请求权的问题上,日本民法的母法应该是法国法,而不是德国法。原因在于,在《德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从肯定了间接受害人请求权的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om
第一草案到否定该请求权的第二草案,起草委员会曾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若认为日本民法立法时在这个问题上从法国法转向了德国法,当然也会存在类似的争论,但立法过程中并无这样的争论。虽然有人主张《民法》第709条否定了间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只是在第711条予以例外肯定,但山口成树教授认为这一主张并无充分根据,而是认为日本《民法》与法国法一样,对此持肯定的立场。法典起草者只是设定了权利侵害的要件,而就因果关系的问题,则交由法官去判断,表明了其对法官的信赖。但与此相反,德国民法起草当时,充斥的是对法官的不信任,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虽然起草者信赖法官的判断,但到了昭和40年代,以相当因果关系划定赔偿范围的随意性被大加批判,其中就有领导东京地方法院民事第27部的仓田卓次法官。山口教授认为,法官背叛了起草者对其的信赖,反倒自己希望被束缚,这无疑是令人讥讽的。[26]在此基础上,山口教授认为,侵权行为致使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发生精神疾病等精神损害时,请求赔偿第711条规定的近亲属固有抚慰金并不足取。并认为,无论是从立法沿革还是从文义上来说,日本《民法》第709条并未限定请求权人的范围;因此,采用是否针对间接受害人也构成侵权的独立构成进而舍却了间接受害人,有可能会导致纠纷解决的僵化,进而不得不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这种路径本身就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弯路。山口教授认为,针对直接受害人的加害行为给间接受害人也造成了损害时,应将间接受害人也纳人请求权人的范围,并采纳灵活的赔偿范围说更为合适。同时认为,英国法、德国法的经验,例如,人员、时间、场所的近邻(接近、密切)程度,特别危险还是一般生活危险等判断标准,对于日本民法背景下的划定赔偿范围的因果关系判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27]
关于间接受害人的损害的定位有两种可能的选择:(1)定位为赔偿范围的问题;(2)作为“权利侵害”要件的解释定位为侵权行为的成立问题或是请求权主体问题。日本有不少学者与山口教授持同样的观点,即认为应将其作为赔偿范围的问题加以考虑。例如,平井宜雄教授认为,虽然(2)的观点,与请求权主体原则上限于受害人的德国损害赔偿法的基本构造具有亲和性,但日本《民法》第709条源于并不存在如此限定的法国《民法》第1382条,作为第709条的解释论,(1)的观点更适合日本民法的构造。[28]同样地,吉田邦彦教授介绍了法国法的审判实践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持相同的观点。[29]另外,前田阳一教授也认为:(1)起草者曾言及法国民法拥有这样的构造;(2)法国的学说也认为遭受损害的所有人都可以请求赔偿,间接受害人的问题被作为因果关系或者是赔偿范围的问题对待;(3)在继受了法国法的波阿索那德草案及日本旧民法中,间接受害人的损害都被作为赔偿范围的问题加以处理;(4)日本民法的起草者也并没有将请求权人限定于直接受害人。[30]当然,前田阳一教授也认为,虽然法国民法并未限定死者近亲属的抚慰金请求,但日本《民法》第711条却限制了死者近亲属的范围,表明了间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问题与财产损害不同,需要另外的考虑。[31]
对于赔偿范围说从日本《民法》第709条母法来源的法国法属性作出解释的立场,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了法国法与日本法在近亲属间接损害问题上的差异所在。该学者指出,法国判例中关于间接受害人问题的定位与日本法(尤其是赔偿范围说)并不相同。在法国法中,以间接受害人是否存在利益侵害为问题核心,若存在利益侵害,则进一步认定于此情形的损害。其中,间接受害人本身是否构成侵权行为是问题的关键。而日本法则不同,其是以对直接受害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为基准探讨该人是否存在损害赔偿请求权,然后判断该直接受害人与间接受害人的关系是否在“相当因果关系”的范围之内,进而决定间接受害人是否得以请求赔偿。也就是说,在日本,损害被作为事实概念对待,以一个侵权行为为基准,然后考量该行为的损害可扩展到何处,在损害赔偿范围的框架内处理间接受害人的问题;作为侵权行为成立要件的损害被限定在初始加害行为所指向的利益侵害,而后续的利益侵害则被定位为赔偿范围的问题;其考虑的侵权行为在数量上只有一个。与此不同,在法国法上,考量的是就各个主体是否成立侵权行为。法国法上侵权行为成立的基础在于规范的“损害”概念,甚至可以说,遭受“损害”的受害人人数决定了侵权行为的个数。对于间接受害人来说,其本身是否明确存在被侵害利益,构成了损害及侵权行为成立的关键。据此,该学者认为,以被侵害利益为基础的规范的损害概念为工具,考察就各个间接受害人是否成立固有的侵权行为,可以避免损害赔偿范围说所伴随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论难点,且也符合民法起草者的观点。[32]此外,在直接受害人受伤、尤其是直接受害人留有后遗症时的近亲属抚慰金问题上,因对日本《民法》第711条有不同的理解,也呈现出了不同的主张。例如,主张第711条确认或推定规定说的学者中,有主张依第709条、第710条肯定近亲属的抚慰金请求,其扩大的范围并不限于与死亡相匹敌的情形;[33]主张第711条为创设规定或限制性规定的学说则多主张类推适用第711条,[34]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予以例外肯定。当然,在主张限制规定说的学者当中,也有认为,虽然《民法》第711条将其限定为死亡的情形,但可以想象到与受害人共同生活的人照料之辛苦,护理会带来相当的精神痛苦,作为其例外,可以依据第709条、第711条肯定其固有的抚慰金请求。[35]
总之,因日本《民法》第709条并未限定请求权主体,利用何种构成来限制间接受害人的请求权,成为日本学说中的重要问题。无论是请求权主体说还是损害赔偿范围说,认为损害赔偿法的目的首先要保护直接受害人,若广泛地肯定间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对加害人来说会带来过重的负担,有必要对此作出限制。而在限制的程度上,请求权主体说倾向于原则上否定间接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除非其符合日本《民法》第711条规定的例外情况或对间接受害人也构成侵权;赔偿范围说则从日本《民法》第709条及第710条的解释出发,试图将其纳人损害赔偿的考量范围之内,此时,相当因果关系以及政策性考量都会纳入其衡量范围。较之请求权主体说,赔偿范围说更容易肯定间接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请求权主体说在责任构成上简洁明快,但就近亲属所遭受的精神痛苦、财产损害等不予以赔偿,是否能符合一般大众的法感情,殊值探讨。但另一方面,赔偿范围说无法避免陷入个案具体衡量的结局,进而无法提供一种更为明确的、可供司法实务操作的方案。较之日本学说的争议,我国学界目前对此尚未有足够的学说展开。但从上述“林玉暖案”法官评析中也可以看出,[36]至少主审法官已经意识到了请求权主体问题及赔偿范围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说介入的连接点所在。(三)日本的审判实践状况关于近亲属的间接损害问题,主要围绕日本《民法》第711条规定的近亲属范围是否应扩大以及直接受害人受伤时是否也应肯定近亲属固有的抚慰金请求权而展开。因“林玉暖案”仅涉及受伤情形,这里仅介绍后者的司法实践状况。[37]
关于直接受害人受伤时是否也应肯定近亲属固有的抚慰金请求权,大审院时代的判例通常持否定结论。其主要理由是第711条的反对解释,认为该条仅在生命受侵害情形下肯定特定近亲属的固有抚慰金请求。但日本最高法院后来逐渐肯定了受伤情形下的近亲属固有抚慰金请求。例如,10岁的女儿因交通事故容貌留有重大伤害,法院肯定了其母亲(父亲在二战中死亡)固有的抚慰金请求。[38]虽然判例的直接依据是第709条、第710条,但学说多认为是第711条的类推适用,原因在于判例要求与死亡相匹敌的情形,实质上是第711条规定的死亡情形的扩大解释。该案后,12岁的女儿因受侵害而受伤,法院认为父母担忧女儿将来能否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等所产生的精神痛苦,并不劣于因女儿发生死亡情形而产生的精神痛苦,也肯定了父母的抚慰金请求。[39]再如,7岁的男孩,因交通事故被诊断为不得不截肢,但经过父母长时间的无私照料和护理而奇迹般地避免了截肢,该案也将范围扩大到了死亡之外。[40]这些判例确立的判例法理认为,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致使身体受伤害者的父母,若因此遭受可以与受害人死亡时相匹敌的,或者是与之相比尤甚程度的精神痛苦的,该父母可以以自己的权利请求抚慰金。但此后,日本最高法院收紧了其一度缓和的尺度,虽然运用的是同样的判例法理,结论上却多否定父母的抚慰金请求。这样的判决也不在少数,如最判昭和42年5月30日民集21卷4号第961页、最判昭和42年6月13日民集21卷6号第1447页、[41]最判昭和43年9月19日民集22卷9号第1923页、最判昭和44年4月22日判时558号第57页等。判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其变更了法理标准,但其适用明显日益严格。学者认为其本质上是从第709条、第710条的直接适用转换成了对第711条的类推适用。[42]鉴于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一变化,日本地方法院审判实务中,在对待直接受害人受伤情形的近亲属抚慰金请求上,其具体判断也出现了分化。现整理近年来的若干案例作一说明。
其中,持肯定见解的案件有诸如松山地判平成11年8月27日判时1729号第75页、[43]大阪地判平成12年2月28日交民集33卷1号329页、[44]奈良地裁葛城支判平成11年8月20日判时1729号第62页、[45]大阪高判平成14年4月17日判时1808号第78页、[46]埼玉地判平成17年2月28日交通民集38卷1号第299页、[47]千叶地裁佐仓支判平成18年9月27日判时1967号第108页、[48]神户地判平成19年6月28日交通民集40卷3号第835页、[49]鹿儿岛地判平成21年6月3日自保杂志1822号第18页、[50]神户地判平成21年8月3日交通民集42卷4号第964页、[51]仙台地判平成21年11月17日交通民集42卷6号第1498页、[52]名古屋地判平成21年12月15日自保杂志1822号第90页、[53]大阪地判平成22年3月15日交通民集43卷2号第346页、[54]大阪地判平成22年5月25日交通民集43卷3号第665页、[55]千叶地判平成22年5月.28日自保杂志1853号第40页、[56]东京地判平成23年6月24日[57]等案件。当然,也有一部分案件持否定见解。例如,除了前述东京地判平成22年1月27日一案以外,大阪地判昭和51年7月15日判时836号第85页、[58]大阪高判平成19年4月26日判时1988号第16页、[59]东京高判平成22年9月30日[60]等案件也都持否定见解。
从这些案件可以看出,直接受害人受伤之情形是否肯定其近亲属固有的抚慰金请求,关键在于该近亲属是否因此遭受可以与直接受害人死亡时相匹敌的,或者是与之相比尤甚程度的精神痛苦。日本最高法院确立的这一判例法理在各级法院审判实践中也得到了贯彻。从地方法院的案件情况来看,直接受害人是否留有后遗症、后遗症的内容及程度,以及近亲属对直接受害人的照料辛劳程度等均构成了具体判断的重要标准;同时,这也成为了抚慰金金额的衡量因素之一。就目前来看,地方法院基本上遵循了最高法院日益收紧的判例态度,在直接受害人留有丑陋疤痕、容貌毁损等情形,其父母通常已不能像最高法院当初确立判例法理时那样容易地得到抚慰金赔偿,转而更多地关注是否留有后遗症及其程度。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留有后遗症的场合,除了近亲属本身的精神痛苦,正如我国俗语“久病床前无孝子”所表明的那样,近亲属照料的辛劳也成为非常重要的判断因素之一。当然,也有部分案件并非是后遗症案件相关的案件,法院仍然肯定了其近亲属的固有抚慰金请求,如前述东京地判平成23年6月24日一案,其父亲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程度成为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林玉暖案”中,法院判决认为,“原告目睹儿子血流满面,精神必定痛苦,有抚慰的必要,法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2000元”。但是,对于类似的目睹现场而遭受打击本身的精神损害问题,日本法院则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例如,东京地判平成22年1月27日一案中,日本法院认为目睹配偶被打伤昏迷所遭受的精神打击,并不足以构成固有的抚慰金请求。大阪高判平成19年4月26日判时1988号第16页一案也否定了直接受害人妹妹目睹现场所遭受精神痛苦的抚慰金请求。在东京地判平成19年6月27日交通民集40卷3号第816页一案中,一起玩耍的伙伴以遭受事故现场的强烈冲击为由请求医疗费和抚慰金赔偿,也并未得到法院的支持。
除了上述抚慰金问题,近亲属因直接受害人受伤而支出医疗费、因直接受害人受伤致使近亲属自身健康受损而人院治疗时支出的医疗费、受害人治疗过程中近亲属支出的护理费、因近亲属护理而引起的停业损害(误工损害),以及支出了丧葬费的情形等,近亲属是否能就其支出请求损害赔偿,会成为问题。这些损害项目中,可以认为大部分只不过是受害人本人遭受的损害转换成了近亲属的损害。即使是丧葬费用,其实质也是受害人本人所遭受的损害。但是,受害人的近亲属因惊吓住院而支出的医疗费、因护理而误工的误工费,以及为了参加葬礼而支出的交通费等,近亲属是否得以将其作为自己的损害请求损害赔偿,则存在争论。[61]在东京地判昭和46年10月26日判夕271号第231页一案中,母亲因丧子而病重,请求因病重而遭受的财产损害(母亲自身的医疗费及住院期间的误工费),法院驳回其请求,而只是将其作为计算抚慰金金额时的斟酌事由。[62]但是,因丈夫受伤而休业的妻子的休业损害(误工费)、参加葬礼而支出的国际航空费、母亲受伤时因护理需要而支出的航空费(最判昭和49年4月25日民集28卷3号447页)、女儿照料受害人时的相当于护理费的损害(最判昭和46年6月29日民集25卷4号50页)等,则有不少案例予以肯定。[63]我国“林玉暖案”中涉及的是其母亲因目睹侵害现场而病倒所支出的医疗费,因此,这里也主要介绍日本有关这方面的案件。在日本,传统的实务标准都是求诸于相当因果关系论,通常会以不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为由否定其赔偿请求,其中就有否定因为护理直接受害人而病倒所支出的医疗费请求的案例。[64]关于“林玉暖案”中涉及的间接受害人医疗费问题,除了前述东京地判平成15年12月18日交通民集36卷6号1623页一案以外,最近的司法实务主要围绕间接受害人PTSD发病问题展开。
大阪高判平成14年4月17日判时1808号第78页一案,二审法院将其母亲患上PTSD的事实,作为考量第711条抚慰金数额的情节,认定了较之受害人父亲更多的抚慰金金额;但并未支持医疗费赔偿请求。在京都地判平成19年10月9日判夕1266号第262页一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原告等人在事故发生当时,在直接受害人的近处,目睹了事故及其结果,但原告等人并非本案侵权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原告等人患上精神疾病等引起的损害,不能视为本案事故引起的损害。”但在考虑近亲属固有的抚慰金时,法院将目睹事故全过程及患上精神疾病等作为抚慰金金额的斟酌情节,分别肯定了父母各300万日元、姐姐150万日元的抚慰金赔偿。东京地判平成20年7月7日交通民集41卷4号908页一案中,直接受害人的女儿主张因该事故患上PTSD致使一年以上不能从事家务劳动,要求误工费、医疗费等的赔偿。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对该女儿的注意义务违反,即使肯定该女儿因此引起各种精神症状的事实因果关系,也难以肯定其存在相当因果关系,故驳回其请求。但在考虑该女儿固有的抚慰金金额时,法院认为,该事故发生当时其在现场、且因此出现了一定的精神症状,不管其是否构成PTSD,均不能否定该事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病,并综合考虑其他情事,给予300万日元的抚慰金赔偿。上述案例表明,源于直接受害人伤亡而引起的近亲属自身健康受害或无法工作等导致的损害,作为近亲属自身的损害,是否得以赔偿,日本法院持否定性态度,而只是将其作为近亲属请求抚慰金时的斟酌事由对待。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三、《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及其解读“林玉暖案”是《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运用,法官利用扩大解释对直接受害人的母亲所遭受医疗费损失和精神痛苦予以酌情赔偿。但在《侵权责任法》背景下,又当如何解释?
对于日本学说主张的不真正间接损害问题,《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2款已经做了明确规定,[65]因而存在的问题不大。问题就在于近亲属等的真正间接损害。下文以《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中心,结合前述日本立法、学说及实践作一简要的分析。《侵权责任法》第3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在其第18条明确规定了被侵权人死亡时的请求权人。从文义解释上言,《侵权责任法》将侵权责任请求权的主体限定于“被侵权人”,并规定了“被侵权人死亡”时的例外情形。同时,在第22条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中,也只是规定“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并不存在类似日本《民法》第711条的近亲属固有抚慰金请求权的规定,也并未明文规定被侵权人死亡时近亲属是否得以请求其自身的固有抚慰金。即使根据第18条规定,由近亲属请求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其请求的也只是“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而不是近亲属固有的精神损害赔偿。在这点上,我国《侵权责任法》与日本民法的立法规定存在较大差异。然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规定了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时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66]《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了因死者人格或遗体受侵害而遭受精神痛苦的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与日本《民法》第711条的规定具有类似性。但与此同时,《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规定侵权责任的承担“应当依照本法”,同时在其第5条又明确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如此一来,如何处理《侵权责任法》与《民法通则》相关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之一。[67]若认为司法解释的规定仍然有效,[68]将《侵权责任法》和司法解释做整体式的理解,其可能的解释就是:原则上,我国侵权法只肯定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在被侵权人死亡或死者人格及遗体遭受侵害时,则肯定特定近亲属自身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样一来,日本学说中的“创设规定说”就具有了参考意义。即《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及《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被视为例外规定,此时的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需要针对该近亲属的直接权益侵害要件及过错要件。若如此理解,能否将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扩张至死亡以外的情形,就会面临与日本学说一样的问题,可能会导向消极的结论。另外,我国《侵权责任法》与经判例学说推动后的日本《民法》第709条一样,利益也是侵权法的保护对象。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及第6条的规定,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虽然学者多主张权利和利益应区别保护,但就《侵权责任法》第2条和第6条的文义解释而言,两者被同等保护。[69]若是如此,虽然近亲属就直接受害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无法享有权利,但就其对直接受害人所享有的“情感利益”等也就有可能构成侵权法保护的对象。这样一来,因目睹死伤事故而引起的健康受损及精神痛苦,也完全有可能纳入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作为所谓的“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也完全可以构成《侵权责任法》第3条意义上的“被侵权人”。但是,即使构成“被侵权人”,也须“依照本法”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此时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需要符合《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的构成要件。也就是说,“过错”要件必不可少。
但在间接损害情形下,对于如何理解过错,尤其是对于如何理解过失的问题上,势必会导致不可能的“拟制过失”问题,进而仍然会推向消极的结论,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故意,原则上此等“情感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同样会面临日本《民法》第711条规定的情形是否应扩张至受伤情形的难题。若对《侵权责任法》第6条做限缩解释,就我国侵权法保护对象的权利和利益采区别说,[70]对利益的保护科以特别的要件,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时,即使将间接受害情形的“利益”理解为近亲属自身的健康、精神利益而不是“情感利益”,也同样会面临过错要件的难题。因此,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与日本略有区别,但所面临的难题基本相同。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框架内,无法给出一个非常明确而统一的答案。若因政策考量试图给特定的近亲属予以保护,可能的解释方案有以下两种。一是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条的基础上做目的性扩张解释,在扩张的同时,应考虑如何限制其边界,以避免对行动自由保障造成的危害。
日本审判实践中所采取的视同死亡程度的精神痛苦这一标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具体衡量因素中,直接受害人的后遗症或伤残程度对于近亲属固有精神抚慰金的有无及数额的影响这一衡量因素,也同样具有参考意义。但是,日本审判实践中将间接受害人本身的健康受损只是作为抚慰金数额的斟酌事由对待这一点,是否值得我国司法实践借鉴,有待进一步考察。毕竟有不少日本学者已指出抚慰金的金额受到司法政策等的制约,不可能太高,很有可能无法弥补间接受害人因此支出的医疗费等财产损失,并认为可借鉴英国法、德国法的经验,利用人员、时间、场所的接近程度等判断标准,判断是否给予间接受害人保护。[71]实际上,在“林玉暖案”中,法院重点关注“目睹血流满面”这一因素,也正是立足于其“近接性”。但这一方案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个案衡量,无法给出非常明确的衡量标准。二是《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的公平分担损失的规则,是否可以适用于间接侵害的情形。该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然而,作为其来源的《民法通则》第132条公平责任原则饱受诟病,第24条在表述上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难以避免适用及适用标准的随意性问题。不过,若政策考量特定情形应当给予间接受害人一定的补偿,除了上述目的性扩大解释之外,第24条的规定无疑是有可能得到援引的条文之一。但是,该条与目的性扩大解释一样,都会面临如何限制其边界的问题。在考量分担损失是否具有合理性时,直接受害人的后遗症内容及程度、近亲属照料直接受害人之辛劳、间接受害人本身的受损情况以及近接性等标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四、结语
综上,就间接损害问题,在判例和学说的推动下,日本在《民法》第711条之外逐渐肯定了因直接受害人遭受伤害而致使特定近亲属遭受“视同死亡程度的精神痛苦”时的精神抚慰金请求,并将间接受害人因此而引起的健康受损作为抚慰金金额的斟酌因素。但对于因直接受害人遭受伤亡而引起的间接受害人本身健康受损所导致的医疗费损失,虽然有不少学说在积极主张,但日本司法实践中仍持慎重态度。在这点上,“林玉暖案”明确肯定了医疗费的酌情赔偿,较之日本司法实践展现了更多的开拓性。不过,是否应当肯定受伤情形的间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及医疗费损失赔偿,现行《侵权责任法》及其司法解释面临着与日本民法类似的难题。即除非故意以侵害特定对象(间接受害人)的健康或致使其精神痛苦为目的而侵害其近亲属的身体、健康等特定情形,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很难得出直接的结论。若对此予以肯定,无论是采取目的性扩张解释还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24条,都会面临如何限制其边界的问题。日本法的学说和实践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我国未来采取何种标准,尚待司法实践和学说的共同推进,以实现法律适用的普遍性、连续性和稳定性。